一條大路通羅馬:浮光
這不是你印像中的羅馬,這不是你想像中的電影,《一條大路通羅馬》標舉了藝術大旗,以文學筆觸來書寫人間風景,挑戰著你的觀影習慣。


觀賞《一條大路通羅馬》(Sacro GRA)之前,能先了解以下三個前提,或許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首先,如果你不知道《一條大路通羅馬》是一部紀錄片,你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為全片沒有劇情,電影中的羅馬,同樣也完全不是你想像的羅馬。但是這部紀錄片又是威尼斯影展舉行七十年以來,第一部獲得金獅獎的紀錄片。
其次,《一條大路通羅馬》既然是紀錄片,為什麼沒有敘述者?沒有議題?更沒有結論?導演Gianfranco Rosi 的美學選擇,樹立了一個創意標竿,卻也同樣是障礙,跨不過去,就容易摔一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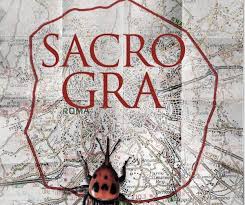
第三,片名指涉的GRA是什麼? 這其實是最好解答的問題,GRA是簡稱縮寫,代表著Grande Raccordo Anulare,指的是圍繞羅馬的一條外環道路,串連周邊市鎮,標號叫A90,全長68.2 公里,開車繞一圈,大約耗時一小時。羅馬市中心的居民大約25萬人,GRA沿線市鎮的居民大約300萬左右,以中下階層居多。
導演Gianfranco Rosi接受訪問時坦承他的影像創作深受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的啟發。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Invible Cities)」中曾借用馬可孛羅與忽必略的對話提到有趣的創作概念:馬可孛羅描述一座橋時,一塊一塊石頭仔細訴說。忽必略有點不解,便問他說:「為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只有橋拱。」馬可孛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了。」細數石頭,正是解讀Rosi創作密碼的關鍵。
Rosi 是義大利人卻是在非洲東北部的小國厄利垂亞出生(當時是義大利的殖民地),十三歲那年才回到羅馬定居,《一條大路通羅馬》就是他對羅馬家鄉的另類凝視,剛巧與去年轟動歐洲的《絕美之城》(La grande bellezza),互成犄角對抗之勢,提供一個羅馬城兩種視野的對照本。

《絕》片是知識份子出入王謝堂前的浮生素描;《一》片則是尋常百姓的營生紀實。前者有飄逸的華麗,因此動人;後者則是蕭索的肅穆,難免有隔。這兩部電影的對照關係,頗適合用卡爾維諾的論述來註解,例如「隱匿的城市之三」中,女巫在求問一座城市的命運時,看見了兩座城市,一個是老鼠之城,一個是燕子之城。老鼠世紀是當代人生,燕子世紀則是未來祈願,兩者都會與時俱變,但是彼此關係並不會改變。
同樣地,「城市與眼睛之二」中也說,賦予X城形式的乃是觀看者的心情。如果你一邊走一邊吹口哨,鼻子在口哨後頭微微上揚,你就會從底部開始認識這座城市;如果你低垂著頭走路...你的目光將會停留在地面上,在排水溝,人孔蓋、魚鱗和廢紙上。《絕》片像是吹口哨走路的旅人;《一》片則是低頭走路的旅人,兩者同樣真實,但是風情卻截然不同。

不過,Rosi選擇的起手式最富興趣味。那是一位老農,直接把針孔插進棕櫚樹,戴起耳機,聆聽著樹心的蟲鳴聲,有鳴就有蟲,有蟲就有病,這位樹大夫聽見了俗人未能聽聞的聲響,診斷出看似一切正常的棕櫚之病。老農的故事,不就說明了Rosi一如這位樹醫,聆聽著最深幽的聲音,要開出對羅馬的文明診斷書?
電影的片頭引用了費里尼的話形容GRA這條羅馬城的外環道路,有如土星的土星環。城在路在,路在城在,沿路而居的人,就此形塑了當代羅馬人的真實情貌,不管是救護車上的勤務人員、沿河網釣鰻魚的漁夫、等待上工的妓女、充滿暴發戶色彩的演員住家...你可以說他們是城市中存活的老鼠,但是有了他們這些石頭,羅馬的拱橋才得以成形,問題在於:你若關心這座橋,你才會細審這些石頭。問題在於,多數人對於這些石頭,既遙遠又陌生,看著看著也就逐漸眼花了。

卡爾維諾在「哲學與文學」一文中曾提到:「哲學與文學是互鬥的對手。」強調哲學將紛雜多樣的存在事物,簡化為一般性觀念,並且制定了法則;但是文學翻轉了這些法則,揭露出一個新秩序;但是哲學家又從中發現了新遊戲規則...哲學與文學的衝突,不需要解決,但是彼此有如不同性質的水晶切面和旋轉軸,隨著不同擺放的位置,光線就會產生不同的折射。羅馬的存在像哲學,羅馬的電影則像文學,兩者拔河吆喝,我們就看到了光影變化。
作者:藍祖蔚
【藍色電影夢】
本期焦點-【v.454】 2014/07/03
其他新鮮事兒

《共犯》誰撿到這本日記,我愛你 (7/3)

恐怖也有東方西方之別? (7/3)

《菜是老的辣》革命家與聖人 (7/3)

《我們最搖擺!》操行零分,友誼滿分 (7/3)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暗黑童話的當代變形 (7/3)

《實習男生存法則》信念崩解的十分鐘 (7/3)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