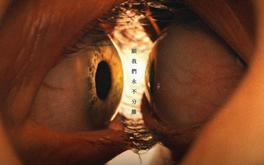作家是一種有病又悲哀的生物──《裸體午餐》
成功的作家是風光的,他們就像《幻想曲》的米老鼠可以揮揮魔杖,失敗的作家則像被自己的魔杖追著打的學徒,他們受困於自己的想像力,並逐漸與外在世界脫節。

《裸體午餐》是一部迷幻又詭異的小說,根據原作者威廉布洛斯(William Seward Burroughs)的說法,你可以隨意按照任何順序讀它,而大衛柯能堡的電影版本則是走更加清晰的路線,你幾乎可以知道太陽高高掛在那,藉由畫面的油膩感以及那些總是在飲酒的人們,還有那可以隔著銀幕聞到的費洛蒙,雖然情節詭異,卻能保有其邏輯,告訴我們作家的可悲。
▍作家這種生物
成功的作家是風光的,他們就像《幻想曲》的米老鼠可以揮揮魔杖,呼風喚雨,改變外在世界對他們的看法,而失敗的作家則像被自己的魔杖追著打的學徒,他們受困於自己的想像力,並逐漸與外在世界脫節。
殺蟲人比爾在「意外」殺死自己偷嗑他殺蟲劑的老婆之後,接到「上層」的指示。拿到船票逃到中介區的比爾,逐漸接受自己得偽裝成「作家」來進行間諜任務的事實。
大衛柯能堡用了一個直觀上有點簡單到蠢的方式告訴我們電影裡大多畫面甚至情節都有高度不可信的成份,比如比爾拿給朋友看的「船票」,在朋友視角其實是藥物,而後面當他拿裝著打字機殘骸的袋子給朋友時,朋友打開一看裡頭也仍然是藥物,大衛柯能堡提示我們眼見不足為憑,或至少你不能用表面上的樣貌來解讀片中發生的事情,所以雖然《裸體午餐》有間諜情節,卻不是諜報片,雖然有外星人,卻不是科幻片,它是一場旅程,卻哪裡都到不了。
它是作家的個人地獄,我甚至懷疑朋友後面找到躲在中介區的比爾時,這段情節是不是也是比爾的個人幻想,在幻想裡,他幾乎完成了名為《裸體午餐》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有朋友能夠來到這個像是東方主義印象下的神祕地帶,且不再跟他談論任何他被通緝(假使他確實殺了自己妻子)的事情,彷彿這件事沒發生過,而僅專注在他的作品,兩個朋友興奮的告訴他,他可能會是他們三個名不經傳的傢伙裡第一個出書的。
然而在他與兩個朋友第一次會面時,比爾不就否定了想做作家的意圖了嗎?
此外,現實也不斷的湧出異化比爾的幻想,所以比爾一直說著自己不能回家,家裡有什麼?或許在這個故事裡,比爾的妻子瓊根本就沒被他殺死,他之所以不能回家,僅是因為自己過於失敗,所以不想回去面對妻子而已。
 《裸體午餐》劇照
《裸體午餐》劇照
▍那些創作的工具
今日看《裸體午餐》,不知怎的會令人想到韓國導演洪常秀電影裡那些無能又自大,愛女又貶女的男人們,他們通常被設定為導演、詩人、或者其他文藝類知識分子,時常充滿慾望,表達的方式卻又蠢到讓人覺得那種欠缺自身專業的表現方式讓他們很失格,他們喜歡編織各種顯而易見的謊言與藉口(而這讓他們很失格的原因是他們應該要對此很熟稔才對,那是他們的專業)而在《裸體午餐》裡,則是對女性、同性,甚至是自己的打字機、自己的作家身分的矛盾感受,為了要處理這樣的矛盾感受,一切事物必須以怪異的方式變形,從不可見的怪異具現化為可見的怪異,那是各種奇怪的人物、事件,乃至於一個充滿巨大的水生巴西蜈蚣的奇怪地帶,還有隱藏於這一切的陰謀與機構。
比如比爾的老婆瓊,透過既是與中介區高層的聯絡人也是打字機的打字機蟲子的說法,首先說她「不是人」,並說她也是「間諜」,而後面比爾追問之前這件事時,蟲子坦承牠真正的意思是「女人不是一種人類」、「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種類,在地表上具有不同的意志和用途」,而片中由奇怪的會下蠱的,有女同志傾向傭人所控制的伊斯蘭女人們看起來也是鬼鬼祟祟的樣子。
不過另一方面這些怪異背後卻有一種清明,當傭人扒開衣服露出胸部後,又可以再撕開,裡面是另個女人嗎?不,是男人,這也強化了整個故事是比爾幻想的可能性,女人都不是實際上的女人,而是他想像出來,單純為某些目的服務的工具而已,如此解讀我們便能更加理解蟲子的意思。
當然對同志與同志性行為的恐懼也可以看做對女人恐懼的延伸(所以片中的男同志全是陰柔型的),所以比爾害怕自己這一面被發現,甚至丟包幫助自己的同志男孩給一個變身怪物的同志富豪,但他逃得了嗎?不,因為如他所言,他的家族流著這樣的血液,於是如同他明明想當作家卻必須藉由間諜行動的「打報告」來使得「寫作」合理化,與同志們的互動同時也必須藏在「打探情報」的功利性下。
▍甲蟲打字機
至於甲蟲打字機,那可真是說出作家的心聲,作為陪伴作家最久的工具(放在現在可能就是筆電),打字機不只記錄著作家的想法,有時甚至可以引導出作家的想法,於是會說話的甲蟲不只可以被打,可以被打到高潮呻吟,更可以與不可見的更高存在連結,進而在多方面消解作家的孤獨,但另一方面作家又很厭惡打字機,因為打字機剝奪了他與其他人正常互動的時間,而且總是不斷吸引他去觸碰他,寫作既是痛苦也是一種歡愉,就像某種帶有梅毒與愛滋風險的性行為一樣。
 《裸體午餐》劇照
《裸體午餐》劇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比爾一開始如此嫌棄自己的打字機,後面卻還是要將牠換回來的原因,他戒不了自己的打字機,如同他戒不了那一罐罐藥物。
電影末段,當比爾總算救出長得像瓊一樣的女人後,兩人乘車來到乍看新的,一個名為「安尼克夏」的地方時,為了要向守衛證明他是作家,他做的不是現場吟詩或者拿出自己的稿件,而是如一開始般拿出手槍要跟妻子玩「試膽遊戲」並再次射殺妻子,然而守衛卻沒有感到驚訝,反而像是看到證件一樣告訴他:
「你通過測試了」
「歡迎來到安尼克夏」
這種帶有惡趣味的安排既可笑也悲哀,昭示了作家的可悲宿命,即便離不開現實,他們卻必須射殺現實,然後一次次的呼喚她回來,然後再度射殺她。
飾演比爾的彼得威勒是經典電影《機器戰警》的扮演者,他有一雙如機器般冷靜的眼睛,而這讓他在本片裡看起來更不正常,因為當周遭的一切都很不正常時,能保持正常的人本身就很難正常到哪裡去。
當然,這也讓他有一股迷人的魅力。
《裸體午餐》看來荒唐且荒誕,卻飽含落魄作家的孤獨與辛酸,他們是沒有登記在案也沒有領處方籤的病人,悲哀的行走在我們的世界,拿著不斷變換的地圖。
「作家跟凡人一樣活在悲慘的現實,唯一的不同是,作家會提出報告。」
.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