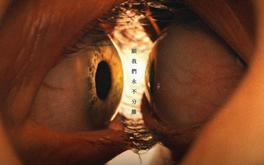複雜的愛,簡單的愛《紅氣球之戀》
本片結局的簡單愛,看似趨向於保守僵化的人際體制,實則蘊含了既逾越超我享樂性命令也逾越象徵秩序禁制性命令的批判精神。而要獲致這樣的愛,豈不是非經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嗎?

每一個人都想愛,都在愛,卻不一定能簡單愛。畢竟,原本簡單的愛也可能突然變得很複雜,更不用說那些自始即令自己與他人痛苦異常的愛了。英國電影《紅氣球之戀》(Enduring Love, 2004)即藉由一起熱氣球意外事故,帶出劇中人接下來發生的虧欠之愛、倒錯(pervert)之愛、偏執(paranoia)之愛,從而探討我們應如何避免愛得複雜難受,以獲致簡單美好的小幸福。
 一個晴朗恬靜的鄉間午後,生物學教授喬(Joe)正準備向女友克萊兒(Claire)求婚,遠處竟飄來一個失控的紅色熱氣球,迫使喬和路人連忙趕往救援。熱氣球在強風助勢下快速上升,多數人因而同時鬆手,剩下老醫生羅根(Logan)不及放手,被帶往高空,最後活活墜地身亡。
一個晴朗恬靜的鄉間午後,生物學教授喬(Joe)正準備向女友克萊兒(Claire)求婚,遠處竟飄來一個失控的紅色熱氣球,迫使喬和路人連忙趕往救援。熱氣球在強風助勢下快速上升,多數人因而同時鬆手,剩下老醫生羅根(Logan)不及放手,被帶往高空,最後活活墜地身亡。
喬自此不斷質問自己是否首先放手而害死羅根;雖然克萊兒不斷開導喬,喬仍舊深陷於強烈的罪惡感。正如Slavoj Zizek所言:「我們愈是順從超我(superego)的命令,它的壓力就愈大,我們就愈發產生罪惡感。」這也就是說,喬愈是想要否定、放棄當初放手時所必然存在的求生欲望,以服從超我律令,就不免恰恰證立了他的罪惡,甚至於更加有罪。
正是喬深陷於超我惡性循環所帶來的無窮罪惡感,再加上他對於阿德(Jed)的異常關注,亦即正是喬對於他人莫名的「虧欠之愛」,終於讓克萊兒感到不受重視與難以忍受,而提出分手。
 相對於喬在超我命令下深陷罪惡感與虧欠之愛的折磨,外表善良、溫柔、失落的阿德則再現了「倒錯之愛」。阿德在足以引發強烈精神創傷的熱氣球意外事故之後,面對深不可測的意義空白,乃是立即獲得了「解答」。他真誠地以為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因而開始祈禱,甚至因為「上帝的撮合」而熱烈地愛上喬、追蹤喬,還刺傷克萊兒。
相對於喬在超我命令下深陷罪惡感與虧欠之愛的折磨,外表善良、溫柔、失落的阿德則再現了「倒錯之愛」。阿德在足以引發強烈精神創傷的熱氣球意外事故之後,面對深不可測的意義空白,乃是立即獲得了「解答」。他真誠地以為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因而開始祈禱,甚至因為「上帝的撮合」而熱烈地愛上喬、追蹤喬,還刺傷克萊兒。
然而既然「上帝安排」、「上帝撮合」毫無道理,那麼阿德他之所以狂信,便是為了逃避事故所引發的精神創傷與意義空白,而將自己基進地轉化為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工具與客體──他是作為讓上帝享樂的工具而瘋狂愛喬。當然,阿德精神形構中的上帝∕大他者不再是由賦予世界事物象徵意義的宗教主符徵(master signifier)所佔據,而毋寧是由小客體(objet petit a)所體現。
另外,羅根太太戲份雖少,卻也有其對照性的角色。面對丈夫意外橫死所引發的精神創傷,她出人意料地不在乎喬是否有責任,反而因為在丈夫車上尋獲野餐食物與女用絲巾,而陷入不斷猜忌、妒恨、驚恐不安的「偏執之愛」。她懷疑婚後丈夫對自己愈來愈冷淡的原因就是狐狸精,更進而對自己偏執幻見(fantasy)中的狐狸精迸發強烈恨意:「她敢接近我家,我就要殺了她!」
 喬的虧欠之愛、阿德的倒錯之愛、羅根太太的偏執之愛固然均以自我對於他人的情感投注作為前提,卻因為方式不當,反而讓愛變得複雜,既傷害他人,自己也不好受。
喬的虧欠之愛、阿德的倒錯之愛、羅根太太的偏執之愛固然均以自我對於他人的情感投注作為前提,卻因為方式不當,反而讓愛變得複雜,既傷害他人,自己也不好受。
本片因而以克萊兒在片尾對喬所說的一句話──「什麼話都不必說」──,暗示了愛其實也可以很簡單,無須象徵誓言與激情享樂。不過,與其說這是純粹的簡單,不如說這是經歷複雜紛亂之後,對於愛的真諦有所體悟的簡單。於是,本片結局的簡單愛,看似趨向於保守僵化的人際體制,實則蘊含了既逾越超我享樂性命令也逾越象徵秩序禁制性命令的批判精神。而要獲致這樣的愛,豈不是非經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嗎?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