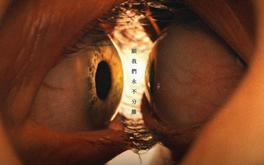是題材選擇了我:專訪《軍中樂園》豆導
豆導坦言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軍艦事件,當時令《軍中樂園》幾乎要難產了,他會堅持下來,兩個原因,「一個就是我拍攝的那段歷史,過了些年,恐怕即將被世人遺忘,那些人的辛酸,那一整輩人的漂泊、那一代年輕人的壓抑,性工作者的辛酸,要是我放棄了,何時才有人幫他們言說?」


豆導鈕承澤嘔心瀝血新作《軍中樂園》浩浩蕩蕩登上大銀幕,片中描繪四十多年前,國共緊張的時局,作為國防前線的金門,其形形色色的人性百態,有軍兵的壓抑與解放,也著墨「特約茶室」陣陣枕邊細語……
說到拍攝本片的緣起,豆導因十年前在副刊閱讀到一則退休老兵的報導,心底轟然一聲雷,大受震撼,「退休老兵們別無選擇地被捲進時代洪流,我在想,他們年輕時也可能很帥、很有抱負,在我腦海裡,若有這麼一部電影,似乎劉德華來演會很合適……」
一場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

之後兩年,豆導的父親過世,這也誘使他重新爬梳這段記憶,「我父親1949年來台,是退休老兵,也是畫家,只是到了四十幾歲,手開始莫名發抖,經醫生診斷後,才知道是漸凍人。當時,我已經演了《小畢的故事》,到處趴趴走,相反地,我爸愈來愈安靜。記得很清楚,他每天坐在客廳藤椅上,思念著大陸的親人,我問他要不要回北京,他不敢,怕終身俸被取消。」伴著焦慮,豆導父親的生命在無法真正團圓的遺憾中慢慢逝去。
「直到有一天,我們跟大陸的三叔連絡上了,他從事京劇表演,赴德國考察,約好幾月幾號幾點,他要打長途電話來。」當時豆導接起電話,還記得話筒內音質不好,像山洞裡的迴音。他將話筒交給爸,父親用彎曲萎縮的手接過話筒,停頓許久,開不了口,後瞬間嚎啕大哭起來……
民國七十年代,父親插上鼻管,活了二十年,意識清醒,沒說過話……「我想像著爸腦內運轉無礙的思鄉愁緒,在我眼中,他太悲慘了,所以我對那個時代那段歷史,有一股刻骨銘心的、想深入挖掘的動力。」
《軍中樂園》在心中,原先的規模僅是小品,想拍出《報告班長》的笑料、《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性啟蒙……

但計畫趕不上變化,去了金門一趟,完全改變豆導對這部片的想法,「對現今的金門,我充滿感覺,尤其看到那個地下的防空砲洞,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或許當時執政當局想像著,若是戰爭開打,這可以用來運輸食物,豈料,這個洞,從來沒有一次以當初建造的目的來使用,換句話說,那場戰爭根本沒有發生。」
這場戰戰兢兢的漫長準備,卻影響了整個金門的人文、生態、思維,那麼多人,都被捲進了這個難分對錯的氛圍、狀態當中,全因一場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
從金門回來後,豆導開始醞釀、琢磨,是不是喜劇,對他來說不重要了。「我不想拍磅礡史詩,那也不是我擅長的。我想走進那個時代,透過這幾個小人物,言說一整個時代的心聲。」
也當然,豆導很怕操作不好,消費了那個時代。但故事發展到最後,他愈有信心,「我知道自己心態上愈形完熟、也愈走近那個時代。儘管題材上看似很政治不正確,但在我心裡,每個侍應生都是我的女神。她們真的是為了這個時代、為了國軍身心靈的需索,糟蹋了自己、奉獻了自己,對她們,我仰望、敬佩。」
考究的佈景陳設,重現小人物心靈風景

作為一個非改編自特定人物事件、卻緊貼舊時代脈搏的文本,豆導積極收集、傾聽很多小故事,吸收、內化,從而轉化出來,而裡面當然也有很多編劇上的分寸須謹慎拿捏。
豆導舉例,在1969年蛙人還不叫海龍,當時他們叫做成功隊,過了兩年才叫海龍。但「海龍」這個名字喊起來,自有一股氣勢——「我挪動這個設定,在情節上是可接受的。」
不過,對於佈景,豆導可就錙銖必較了,從一磚一瓦、道具、服裝,到歌曲,都是經過考據的。其中,當年八三么的洋樓,徵用了很多民宅作為單位據點,「我很著迷洋樓,這些建築神似巴洛克式風格,也有閩南某些廟堂的規模,及一些詩書的況味,你說中西合璧也好、說古今融合也好,總之是很有特色的建築。」
豆導說,跟以黃美清為首的整個美術組,從《艋舺》以來,已經建立了高度默契,「美術組他們很像我的手,或是我腦袋的一部份。這幢洋樓剛找到時,傾頹敗壞,我和美清討論、研究其光影的多種可能,如何凸顯其寫實與華麗,花了很多力氣搞定地權,並花了將近兩千萬裝修,那是很慢很龐雜的過程。美術跟製片,在那邊住了一年,打點一切。」

既忠實時代精神,充分消化調查後得到的基礎。再加上自己的想像,摻雜角色獨特性,去賦予佈景全新的生命,那怕是一本雜誌、一雙拖鞋,都要深入舊時代的私密夾層,觸探各種可能。
光是拿妮妮房間的「風獅爺萬花筒」來說,就搞了很久,「一開始的紙萬花筒,我不喜歡,太華麗又顯得俗氣,有沒有可能賦予萬花筒一個『前傳』,是金門當地一個手藝極佳的師傅,特地做來送她的?我們竭盡想像,前前後後做了五十個,試遍各種可能。」
至於看似簡單的軍服,光是用什麼料子,什麼顏色,什麼光影之下會有什麼變化?每個步驟都是學問。老兵會洗得比較舊,新兵顏色偏深,阮經天戲份多,劇組得做三種軍服,單單這件事情,可能就看過無數布料,在陽光下面比對,「決選」出兩個系列,然後試拍,最後再決定要用哪個顏色,豆導說:「這樣的高標,其實從《艋舺》就開始了。」
戲裡戲外,娓娓道來

比起之前的長片作品大玩華麗運鏡,豆導說,拍《軍中樂園》比較不會想設計鏡頭,因為對時地深有感觸,即興成份也多,這次想踏踏實實地透過每個角色,將故事娓娓道來。
其中有個情境,是無事午后,苗可麗側躺在床,摸撫著牆壁上搖曳的光影,「那個畫面的靈感,是來自我的母親,記得當時我陷入低潮,沒有戲演,跟我媽住一起。一天下午返家,看到我媽背對著我,她身旁的窗,陽光透進來,樹影在牆上頑皮跳動,她就逗著影子玩,像少女一樣,哼著歌。平淡無奇的午后,一個女人的背影,訴盡了多少奉獻與寬容……我受到很大的震撼,這個收藏在我心裡的深刻畫面,趁著這次,就將它給體現出來。」

至於阮經天和萬茜的一場露骨床戲,豆導說,難度倒沒有想像中來得高,「他們都是極其專業的演員,我對萬茜帶著高度期待,我與阮經天的默契更不用多了。當然,過程會有一點緊張,但很專業。拍攝前有大致排練,細節也有『自由發揮』的成分。為了幫他們入戲,我可能會問說,要不要一口高粱。我給了一些必要的指令,去破除他們之間的尷尬,不然,女生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男生不知道能不能那樣。大家都經過很好的溝通,互相信任,順從體內情慾的呼喚,從而把角色當時所受的壓抑,做一個貼切的抒發。」
風雨過後,真心擁抱
豆導坦言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軍艦事件,當時令《軍中樂園》幾乎要難產了,他會堅持下來,兩個原因,「一個就是我拍攝的那段歷史,過了些年,恐怕即將被世人遺忘,那些人的辛酸,那一整輩人的漂泊、那一代年輕人的壓抑,性工作者的辛酸,要是我放棄了,何時才有人幫他們言說?就算有,聲語可能也不一樣了,這是很可惜的。」
第二是團隊。大家已經合作很久,也都承認這次遭逢很大挫折。有一天,大家集合在一塊,滿滿的人。豆導神情凝重地問大家:「還想不想拍?」、「還是有沒有人要離開?」
沒有一個人離開。
「管他的政治立場相不相同,大家驚濤駭浪中,萬眾一心。或許台灣電影經驗不夠、資源不夠,電影工業荒廢已久,但是能從這群人身上看到一種信念與態度,你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價值、陽光還是不錯的……。我們團隊或許很小,可是我們很有志氣、很有活力。我們有很多美好的、小小的價值,它們不應該被負面聲音所吞噬。」

豆導亦有感而發,現下台灣,每到選舉,火藥味隨之湮起,城鄉之間、南北之間,大家沒辦法真心擁抱,以前我們喜歡閱讀成功者的故事,我們羨慕他們,我們激勵自己、我們想努力看齊,現在我們喜歡看失敗者的笑話,我再努力一輩子也買不起一棟房子,憑什麼你混得比我好?我又不比你差。我們看似豐衣足食,可是面對這個混亂的世界,天災人禍不斷,我們常常不快樂。對照《軍中樂園》所描繪的那個荒謬過往,好像有一種荒謬,至今恆常存在。」
行過的,仍是這片土地
選擇這個題材,正是想完成一個心靈儀式。耗資2.5億,從回收角度來看,當然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壓力非常大,豆導表示,有了《Love》那樣的經驗,看似執導合拍片,才是聰明之道,「前年開始,我面對很多誘惑,大陸有人找我拍奇幻大片,片酬也可觀。但我還是推掉了,一心想先將《軍中樂園》完成,從生意的角度,很多人都覺得我瘋了。儘管我不覺得這部片,是這個民族所有人都能夠閱讀的。但其中,有很多人性共通的溫度,是不管哪裡的人都可以體會的。所以也可以說,是這個題材選擇了我。」
他說,自己身為一個祖籍北京的台灣人,當然期待台灣有更大的空間、市場、資源,支持我們拍出更多不一樣的片子。我們不能每部戲都盈虧都精算得一清二楚,電影不是生意而已。有時候不得不做它,是基於心底一股無以言宣的熱度。
「我要講的,聽起來矯情、卻是真心的感受。我很幸運,我能夠遇到這樣的故事、這樣的題材,我能夠拍一部我覺得有意義的電影,就算傾家盪產,那又如何?起碼我每天騎著腳踏車,行過的,仍是這片土地。」
最後,豆導卑微地希望透過團隊的真心誠心、透過這部稱之為努力成果的電影,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我還是期待很好的成績,或者至少證明在台灣可以做這樣的投資,一個好的電影環境,應該百花齊放、延綿不絕。」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