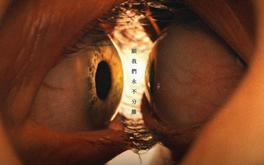《海角七號》:認同的孤島
電影《非關男孩》一開始問了一個問題:「『沒有人是孤島』是誰說的?」休葛蘭說是邦喬飛,這當然是開玩笑。

看完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我想起幾部電影:大衛馬密的《殺人拼圖》、詹姆士葛雷的《萬惡夜總會》、張作驥的《蝴蝶》……然後我想起這首詩。
這幾部電影都和《海角七號》完全不同,而且一部比一部沉重,但是共通之處是它們都碰觸到出身、血緣、歷史、語言等種種關於身分認同的問題。
身分認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辨認?這是個大問題,多少社會迷思正是由彼此區同分異開始的。
 《海角七號》裡幾個角色的身分設定相信台灣觀眾一點都不陌生:原住民交通警察勞馬﹝民雄飾演﹞、客家人賣酒業務馬拉桑﹝馬念先飾演﹞、本省籍機車黑手水蛙﹝夾子小應飾演﹞等人都算簡單明瞭;而當本省籍鎮民代表洪國榮﹝馬如龍飾演﹞對上外省籍飯店經理﹝張魁飾演﹞時就多了些政治況味;年逾70卻不失天真的老郵差國寶茂伯﹝林宗仁飾演﹞想當然耳是台灣人,豈知他可能15歲以前是日本人!至於才10歲就擁有一個老靈魂的教會天才鋼琴手大大﹝麥子飾演﹞則是根本還未「成人」,但她的母親﹝林曉培飾演﹞明明懂日語卻故意裝儍不屑說不想說,她的外婆當年甚至差一點嫁到日本成為日本人!
《海角七號》裡幾個角色的身分設定相信台灣觀眾一點都不陌生:原住民交通警察勞馬﹝民雄飾演﹞、客家人賣酒業務馬拉桑﹝馬念先飾演﹞、本省籍機車黑手水蛙﹝夾子小應飾演﹞等人都算簡單明瞭;而當本省籍鎮民代表洪國榮﹝馬如龍飾演﹞對上外省籍飯店經理﹝張魁飾演﹞時就多了些政治況味;年逾70卻不失天真的老郵差國寶茂伯﹝林宗仁飾演﹞想當然耳是台灣人,豈知他可能15歲以前是日本人!至於才10歲就擁有一個老靈魂的教會天才鋼琴手大大﹝麥子飾演﹞則是根本還未「成人」,但她的母親﹝林曉培飾演﹞明明懂日語卻故意裝儍不屑說不想說,她的外婆當年甚至差一點嫁到日本成為日本人!
而全片的主戲還是落在一個來台打工卻聽不懂台語的日本女生友子﹝田中千繪飾演﹞以及一個懂台語、說國語的「新台灣人」阿嘉﹝范逸臣飾演﹞身上。
但這個「新台灣人」卻是個孤兒。
這個主角為孤兒的設定其實決定了導演的中心意旨,即使我們不知道阿嘉在台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生存不易?懷才不遇?感情不順?﹞,但卻能夠理解他從頭到尾的那些情緒:對現實的怨恨與不滿。
當交通警察勞馬第一次抓到阿嘉騎機車未戴安全帽時,阿嘉指出前後左右沒有一個人有戴安全帽,「為什麼偏偏抓我?」,對於阿嘉的質疑,勞馬的回答是:「你看起來比較倒楣!」此言一出現場每個觀眾似乎都發出會心一笑;重點不只是那個大家都清楚的台灣社會現象,更在於阿嘉的反應正好顯露出他的孤兒意識!
孤兒意識的另一種表現乃是藉由表達自己的處境來引人同情,片末日本歌手中孝介加入合唱的那首舒伯特名曲「野玫瑰」,從詞義來看更是孤兒意識的明證。
孤兒意識本從命運而來,當命運被他人決定自己無力改變時,你看什麼都不對勁,做什麼都不起勁,全世界彷彿都與你為敵;但反過來別人看你也是一樣怎麼看怎麼不順眼,不要說勞馬,就是那個日本女生友子更是受不了,就算真是破銅爛鐵樂團,也不應該這樣不當一回事。為了轉變這個危機,導演設計了一疊60年前的情書。
許多觀眾質疑這個設計和敘事主線的關係薄弱甚至毫無關聯,但我的解讀是:導演希望藉由阿嘉在完成別人由於信任所交付予他的任務時,理解到人其實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重點是你必須要做些什麼﹝do something﹞!
就像60年前那段日台師生戀,正是因為屈服於大時代的命運安排,日籍教師﹝中孝介飾演﹞才會拋棄台灣女子友子﹝梁文音飾演﹞,一個人上了船躲在甲板上偷偷探個頭向她告別,然後在抽屜裡藏著那一疊信藏一輩子;然而如果60年前的感情到今天還能傳達到愛人的手裡,人世間又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阿嘉由於成功遞送出這份情意,讓60年前的悲劇有了一個可以滿意的結局,如果他對自己所熱愛的音樂﹝及女人﹞竟跟60年前的日籍教師一樣畏縮猶豫,那還有什麼搞頭?
 只是複雜的不是劇情如何安排解釋,而是台灣人的孤兒意識在60年後竟還得靠著殖民母國日本的「感召」才得解放,我認為這當中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思索追論的地方。
只是複雜的不是劇情如何安排解釋,而是台灣人的孤兒意識在60年後竟還得靠著殖民母國日本的「感召」才得解放,我認為這當中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思索追論的地方。
荊子馨在「成為『日本人』」一書的最後一章中,藉由詳細分析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提出所謂《基進意識》:「堅持認同形成的矛盾與多元性,並拒絕鐵板一塊的『日本民族性』、『中國民族性』和『台灣民族性』」。
這種「基進意識」,荊子馨說:「是一種辯證性的鬥爭,這種鬥爭體悟到被殖民者可以以不具本質的方式出現在更大的殖民現代性這個母體中。它強調殖民認同形成的偶然性。」
如果我們暫先不對「台灣人」或「新台灣人」進行本質性的區別與定義,則從《亞細亞的孤兒》對應到《海角七號》,恰恰能夠印證荊子馨所提出的「基進意識」。
《亞細亞的孤兒》藉由男主角胡太明不斷地在日本、中國、台灣這三角關係中進行空間的移動,從而不斷產生身分認同上的辨證活動;《海角七號》則恰恰相反,空間是固定在台灣南部恆春小鎮,卻藉由不同身分的人彼此碰撞激盪來進行身分認同上的辨證活動,唯一遺憾的一點是三角關係中缺少了中國這一角﹝你也可以說,中國的不在其實是另一種在﹞。
依照荊子馨的說法,無論是從陳映真式的「中國民族本質論者」或宋澤萊式的「台灣民族本質論者」的角度來看,《海角七號》都是無法令其滿意的:前者一直想解消台灣人的孤兒意識,認為那是回歸的障礙,結果《海角七號》阿嘉反而回頭擁抱日本;後者則強調孤兒意識正是台灣性的本質表現,結果《海角七號》卻出現各種各樣不同身分認同的台灣人──不啻說明死守孤兒意識只會無限擴張變成受害者妄想情結,以阿扁為代表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辯護說詞﹝阿扁說「別人都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跟阿嘉說「為什麼偏偏抓我」有何不同?﹞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旅日作家李長聲在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所著「鏡像下的日本人」的推薦序中說道:「日本人和外國人都相信日本是獨特的國度,在文化、經濟、政治方面,這種認識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點。……布魯瑪解說文化,卻不容許拿文化做擋箭牌,以開脫歷史的責任。」
 強調文化的獨特性乃至自我膨脹其優越性,正是各個民族本質論者經常大言夸夸的表現之一,倘若人人都無限上綱,不是你要同化我,就是我要同化你,最後人與人爭,不是出現「利維坦」,就是同歸於盡。
強調文化的獨特性乃至自我膨脹其優越性,正是各個民族本質論者經常大言夸夸的表現之一,倘若人人都無限上綱,不是你要同化我,就是我要同化你,最後人與人爭,不是出現「利維坦」,就是同歸於盡。
《海角七號》不但以適當的幽默自嘲解消了這一點,同時以阿嘉一句「我操你媽的台北」隱喻了「去中心」的主體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在地性﹝不忘出身﹞,結合歷史與記憶,重新啟動,投注熱情,才有實踐自己理想的可能。
要達成這樣的認知,必須先建立「沒有人是孤島」的信心,張作驥的《蝴蝶》以更細密深刻的經營,卻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電影本身的整體表現其實更勝《海角七號》,只可惜未能得到相當的關注。
最後我想提醒,其實《沒有人是孤島》是馬如龍說的,就在他幫阿嘉保養機車的時候。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