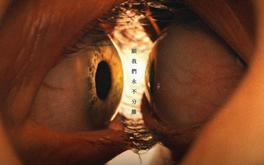一千次晚安:快門勇氣
弘一大師填過一首「落花」詞,「花滿庭,花滿庭,怎奈風聲又雨聲;也可喜,也可驚,一樣看花兩樣情;有人但惜好花落,有人且喜結果成。」同一件事能夠取得多元解讀,同一件事,能有不同時間序的理解,面向和內涵都會更不俗。


對比,是藝文創作的重要手段,透過對比,我們對事物的本質與神髓,因而得著更清楚的輪廓。《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Tusen ganger god natt)選擇的對比手法,有多個層次,關鍵都在照相機的快門。
《一千次晚安》的核心人物是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攝影記者Rebecca,相機是她的吃飯傢伙,冷靜地按下快門則是她紀錄事實,發覺真相的必要手段,就在按下快門的剎那,她是絕情?抑或多情呢?
《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與收尾戲都是Rebecca在阿富汗前線,見證炸彈客的宗教與行動儀式。炸彈客同樣是清純的女郎,抱著必死決心,先躺進死亡的墓穴,接受土葬的預演儀式,再淨身沐浴,著裝綁彈,從容上前線......
Rebecca原本是見證者,冷靜目擊每個流程,精準按下相機快門,但是終場前,她按不下快門了,她跪地長泣,前後判若兩人的心境落差,讓觀眾面對「自殺烈士」的理念與生命困境,取得更深入的觀點。
遇見好新聞,就有見獵心喜的激動,其實是多數記者的本能反應。能夠採訪到自殺客的宗教儀式,多數戰地記者都不願錯過,Rebecca能夠獲准採訪,一方面是擴充眼界,善盡專業本份的難得機會,另一方面則是僅管機會難得,要力保客觀,不能淪為宣傳,但亦不能退縮保守,失去認識或者發現真相的契機。

挪威導演Erik Poppe無意和觀眾討論「攝影」的本質,也無意和大家討論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強調的攝影觀念:「雖然人們會覺得相機確實抓住現實,而不只是解釋現實,但照片跟繪畫一樣,同樣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一千次晚安》的開場戲其實是「獵奇」與「報導」並存的一種現象:自殺炸彈客竟然是女性(相較於傳統的男性死士,這個真相,就取得了比較的能量),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更進一步深思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抗爭思維。
多數戰地攝影記者都有些使命感,出生入死,報導真實,都有著想略盡棉薄,靠著系列照片,力挽狂瀾,幫助殘缺的世界變得好一些。Rebecca同樣有著見不得人生不公不平之事的「怒氣」,拍照成了她的救贖解藥,如非同為女性,她未必能夠深入沐浴著裝現場,取得更多內幕現場照片,為她的報導蓄積更多的震撼能量。
但是,若非Rebecca鍥而不捨,堅持一路跟拍,甚至臨下車時,還要回身補拍兩張,警察會上前盤查嗎?炸彈客會在鬧區引爆炸彈,傷及更多無辜嗎?被震波炸飛也受了傷的Rebecca繼續奮勇按下快門,固然是專業與敬業的表現,然而Rebecca是不是促使炸彈客提前按下引爆鈕的關鍵呢?她是不是以「他人的血」來成就自己事功呢?(「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是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de)的成名作,此處借用書名,來補充戰地記者無可迴避的道德困境)

《一千次晚安》這時候技巧性地用引爆其他話題的方式,迴避了這個矛盾爭議(警察如果攔查Rebecca的相機,或許干預了新聞自由,但會查知更多真相),資助Rebecca前往採訪的出版社受到五角大廈的威脅,不敢採用Rebecca的作品,以免落得美化炸彈客的指控,影響他們在華府的其他採訪(這卻也直接批判了美國霸權的新聞干預手法)。這次挫折,也讓Rebecca順理成章得以扮好媽媽的角色,甚至以陪女兒做報告之名,轉進非洲難民營。
當然,只有再次聽聞槍聲響起,Rebecca血液中的戰地記者本性才會顯現,在母親與記者的雙重角色中,她放下女兒Jessica,追著槍聲跑,趴向前線猛按快門,對乍聞槍響的女兒是一次無情的選擇,生命的天平上,女兒的砝碼,在那一剎那,遠不如死難災民重要,此時的Jessica面對的是內外雙重受創(生死一線間的不確定感,母親又以工作為重的失落感),她的挫敗、憤怒與失望,最後匯聚成她取得母親相機,毫不間斷地按下數十下連拍快門的聲響,就如同不斷打在Rebecc臉上的巴掌。
是的,同樣是快門,Rebecca與Jessica按下的聲響,意義截然不同,有此對比,記者/母親的矛盾,既是高潮,亦是無解的回境。
至於結尾的重回阿富汗前線,重回炸彈客儀式現場,看到更稚嫩的臉龐,看到更年輕的胴體,Rebecca的猶豫與遲疑,道盡了她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她的為難,按不下的快門,對照開場時的一往直前,前線記者的人性掙扎,就此得著更強力的論述。
作者:藍祖蔚

 分享到facebook
分享到facebook